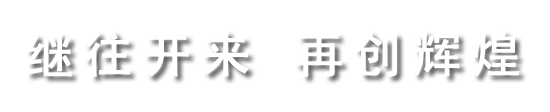骆驼背上的社会主义:论哈萨克斯坦的饥荒历史与苏联的历史责任
雅罗斯拉夫·科瓦楚克:您为什么决定研究哈萨克斯坦的饥荒?是什么吸引了您关注这个话题?
莎拉·卡梅隆:我最初对中亚感兴趣,是因为我认为与苏联别的地方相比,中亚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当时,我是耶鲁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研究苏联历史。当我研究中亚时,我发现许多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乌兹别克斯坦,并以此为例来概括整个中亚。但事实上,当你仔仔细细地观察这些国家和社会时,它们之间其实存在很大差异。我认为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重要的大国。特别难找到西方作者写的关于它的书。因此,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并决定开始有效学习哈萨克语。
那年夏天,我去了哈萨克斯坦,了解了这一个国家的历史。我开始翻阅高中生课本和为哈萨克斯坦学生编写的儿童读物。我看到有关于这场饥荒的记载。我觉得这太令人震惊了。我学了这么多苏联历史课程,却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我注意到,当我提到这场饥荒时,我所在领域的许多领军人物对此都知之甚少。就在那时,我认识到:“天哪!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不仅对于哈萨克斯坦及其历史如此,对我们理解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也具有普遍意义。” 因此,在开始有效学习哈萨克语的那个夏天之后,我决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问:在俄罗斯帝国殖民之前,哈萨克草原的自然环境是怎样的?当时游牧民族面临哪些饥荒风险?
这种环境有几个显著特征。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水资源匮乏。在这种地貌中,水可能特别难找到。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缺乏优质牧场。在适宜农业耕种的地方,优质土壤可能年年都会发生快速变化。
因此,哈萨克游牧民族选择了游牧或放牧。这是对草原环境特征(即牧草和水资源匮乏)的适应。与其说这是一种落后的生活方式,不如说这是对环境特征的适应。有些游牧民族会随着季节变换而迁移,充分的利用这些稀缺的环境资源。
草原的另一个特点是,每年的降雨量可能会出现很大差异。因此,一年可能降雨量很大,而第二年则可能少得多。所以,变化很大。草原会有一段干旱期。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俄罗斯帝国统治下来自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一些首批定居者很难适应草原环境。他们中的许多人饿死了。当局甚至一度禁止在草原上定居。
许多关于集体化的研究都集中在斯大林做出决策的那几年。当然,了解这一点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饥荒,就不会这样研究。人们总是认为饥荒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短期决策,也有更广泛的脆弱性模式。
我在书中想做的一件事是退一步审视俄罗斯帝国在这一地区定居的更悠久历史。我还试图说明,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发生的许多事情使哈萨克人更容易遭受饥荒。这包括改变他们的食物结构,也包括改变迁徙路线。许多这样的事情使哈萨克人更容易遭受饥荒。它不是导致饥荒的原因,但我认为它是一个促成因素。
许多哈萨克人反对革命。首先,我认为整个中亚地区的革命时期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我们应该更多相关著作。对于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许多不同的语言。该地区的许多方言都是用古老的阿拉伯文字书写的。这也给还原历史增加了难度。
但当时,许多哈萨克人反抗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最著名的例子是阿拉什奥尔达,这是一个哈萨克人自己的政府,曾短暂统治过传统上属于中部落哈萨克人土地的地区,即塞米巴拉金斯克周围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塞米伊。他们短暂地拥有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哈萨克政府。
问:革命后,苏联的现代化项目和游牧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兼容,尤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正如你在书中所说的,骑在骆驼上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吗?
这一时期有很多争论。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流动性更大的时期。对于莫斯科来说,游牧生活是个难题,因为它不符合他们从俄罗斯欧洲地区带来的模式。马克思写了关于工人和将革命扩展到工人的文章。然后,你需要再次飞跃,将这个想法扩展到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即正在衰落的俄罗斯帝国。然后,你要进一步飞跃,思考怎么样将它融入游牧社会。
因此,布尔什维克对游牧社会的想法感到困惑。游牧民族是不是真的像定居社会那样有阶级之分?有一种观点认为游牧社会是平等的。最初,有些人甚至认为可以与游牧民族合作,而不是反对他们。他们可能会建立游牧学校和游牧医院。最初,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些证据说明与这种游牧生活方式合作,而不是反对它,试图支持它。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转而反对这种生活方式。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转向了这种经济模式,这种模式需要非常可预测的收益。游牧生活很难适应其中的一些要求。另一个原因是,一些最初支持在下保持游牧生活的人有着所谓的可疑背景——他们有非布尔什维克的背景。对他们的清洗与对这一立场的清洗重叠。
问:您还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给哈萨克斯坦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讨论了民族政策。特里·马丁认为,民族政策属于软性政策,其主要任务是推广社会经济转型所代表的强硬政策。但您认为民族政策和集体化之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您能否详细谈谈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和集体化之间的联系?
在我的书中,我没看到软性和硬性政策之间的区别。许多软性政策可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我认为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区分国籍政策,因为它们通常与这些经济政策密不可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硬性政策,例如集体化,与国籍政策完全相关。其目的不仅在于确保政权获得可靠的粮食和肉类来源,还在于通过定居化发展哈萨克民族。我认为,在实地推行民族政策时,不能把某些政策作为胡萝卜,吸引人们接受。许多哈萨克人了其中一些温和政策。
问: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哈萨克领导人菲利普·戈洛什琴宣布了“小十月”政策。为什么叫“小十月”?这项政策又是什么内容?
我也觉得“小十月”这一个名字很有意思。认为哈萨克人没有经历过十月革命,他们必赶上前俄罗斯帝国别的地方已经经历过的社会革命。因此,这场社会革命通过“没收白布运动”消灭了精英分子。从某一种意义上说,这个群体相当于哈萨克版的富农。于是,他们把目标对准了数百名他们眼中的哈萨克显贵和富人。
这场运动对后来的集体化道路确实很重要,因为它对哈萨克社会造成了分裂。它使哈萨克人相互对立。这是从内部摧毁哈萨克社会的第一步。某些学者可能会将其描述为外部强加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布尔什维克所做事情的真正残酷性。他们试图从内部使人们相互敌对,让哈萨克人对其他哈萨克人实施暴力行为。他们特别授权哈萨克人这样做,并且对运动条款留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这就是1928年没收白布运动,也就是“小十月”运动。集体化直到1930年才开始,但这场运动为集体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并帮助动员了人民,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我认为,我们正真看到了与苏联别的地方相同的动机。有时,政权倾向于针对那些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比如孤儿或社会边缘人群。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有些人出于真正的信仰而加入。他们的信仰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些重叠。我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清算旧账。
布尔什维克通常将此类运动描述为阶级斗争。但我们谈论的是游牧民族,他们没像富农那样的分类。那么,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将这些与哈萨克斯坦农民社会相关的分类运用的呢?
有证据表明,这十分艰难。这个社会绝大多数都是口头文化,而不是书面文化,我们关于哈萨克游牧社会的大部分资料都是由外来者撰写的。他们有自己的偏见和问题,并且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写的。然而,我认为有证据说明,其中一些战斗中存在一些阶级斗争的元素。有些人确实反对白人的统治。在革命前夕,一些富裕的哈萨克人在这里积累了财富,拥有大量牲畜。因此,这可能是一个分裂点。
另一个分歧是氏族分歧。哈萨克人属于超级部落联盟。哈萨克社会中有三个部落,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为了加强自身的氏族而进行的战斗。在这些超级部落联盟中也有氏族。所以,这绝对是一种分歧。我还要说,宗教可能是另一个分歧,教。所以,在这一段时期发生了许多不同的叛乱行为。一些人试图建立一个国家。所以,这可能是我要指出的另一种分裂。
问:您讨论的早期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悖论是牲畜数量急剧减少。那么,您如何解释呢?政策目标不同,莫斯科希望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的主要肉类来源之一。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是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苏联其他计划中看到的例子。命令下达后,许多细节问题才被提出来。但在牲畜问题上,这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例如,他们没想到牲畜分布范围如此之广。他们没想到如何为这些牲畜提供饲料。他们也没有想到,把这些牲畜集中在一起会有什么后果。许多牲畜感染了各种疾病并死亡。
另一件事是许多哈萨克人不想让他们的牲畜被没收。因此,他们通过屠宰牲畜来抵抗。这导致了牲畜数量的急剧下降。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哈萨克人把牲畜放牧到边境以外。这种情况在附近国家尤其普遍,人们把牲畜放牧到边境以外以逃避没收行动。这是集体化的一大讽刺,当然也是意料之外的结果,导致牲畜数量锐减。
另一个原因是,在集体化初期,许多哈萨克人必须满足粮食采购要求。当莫斯科甚至阿拉木图查看哈萨克斯坦地图时,他们向哈萨克斯坦各地区施加了各种采购要求。有时,他们对这些地区的特殊性了解得非常少。住在畜牧区的人必须缴纳粮食采购费。那么,为了满足这些采购要求,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种粮食,人们就必须卖掉牲畜来换取粮食,以满足这些采购要求。
1933年的苏联宣传海报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集体化景象。摄影:马贾尼基金会
问:那么,饥荒从何时开始?如果将哈萨克斯坦的饥荒与乌克兰大饥荒进行比较,在您的书中,哈萨克斯坦的饥荒似乎持续了更长时间。它比乌克兰的饥荒开始得更早。
在哈萨克斯坦,饥荒始于1930年冬季。我认为1931年,饥荒已经非常严重。1932年确实是哈萨克斯坦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我们可以说,饥荒在1933年底结束。我认为哈萨克斯坦饥荒的持续时间非常惊人。而且,正如您所说,它比乌克兰大饥荒开始得更早。
问:但为什么持续时间这么长?如果我们将其与乌克兰大饥荒进行比较,我们知道它持续了1932-33年,然后才派出了救援。但在哈萨克斯坦,持续了几年。为什么执政党没有像在乌克兰那样对此做出反应?
嗯,我们知道斯大林和其他人多次听说哈萨克斯坦发生了饥荒。但他们没采取什么行动。当时人们对游牧生活有很多刻板印象,比如游牧民拥有大量牲畜和囤积食物。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他们多次被告知,而且使用了饥荒这个词。
我认为这是对哈萨克人的一种非人化。甚至可以说是种族主义。从饥饿的哈萨克人受到的对待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一点。他们被当作非人对待。在很多方面,他们被当作流浪者和乞丐。当时,执政党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直到牲畜数量锐减,我们才真正看到他们采取行动。
就我所知,在哈萨克人的案例中,疾病的传播是一个大问题,而在乌克兰人的案例中,情况并非如此严重。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是因为许多哈萨克人开始死亡,而饥荒中常见的现象是,他们死于流行病。由于担心疾病传播,这个问题成为中心关注的一大问题。
还有难民危机。这与乌克兰的情况截然不同。我们还有更多的哈萨克斯坦人正在挨饿,大约有100万人逃离自己的国家,逃往俄罗斯和中亚周边国家。这对这些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呼吁:“嘿,莫斯科,帮帮我们,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
他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集体农场和畜牧场都招不到人,因为大家都逃走了。直到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并试图采取行动。
问:你认为这场饥荒的主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是共和国领导人还是莫斯科?谁该承担什么责任?
嗯,当然是莫斯科,斯大林。在我的书中,我试图稍微缓和一下戈洛什钦的形象,他有时被诬蔑为杀害哈萨克人民的刽子手。他是一位非常残暴的领导人,但我认为也有证据表明,他尽可能地试图减轻或缓和莫斯科的政策。我们首先必须看看莫斯科。
这些政策可怕之处在于,它们本质上也是试图从内部摧毁哈萨克社会,让哈萨克人自相残杀。民众的参与对于这场饥荒的发展至关重要。布尔什维克在动员和激励人民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当然,莫斯科必须承担主要责任。
1932-1934年饥荒时期的哈萨克人。图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国家视频和摄影文件档案馆
问:您已经提到过,许多哈萨克人因饥荒而逃离。哈萨克人对饥荒的总体反应是什么?您如何描述?是逃离、抵抗还是认命?该地区大多数哈萨克人的反应是什么?
哈萨克饥荒中的数字是一个大问题,但对此的探索却少得多。我们没有与乌克兰饥荒相同的统计数据。大饥荒的学者们已经用非常复杂的方法计算了死亡人数。但在哈萨克饥荒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谈论这个话题时发出的主要呼吁之一。我说,我们必须更彻底地研究哈萨克人口问题。只是还没有人做过。我们知道死亡人数众多,但我们确实没有确切的数字,特别是按地区划分的数字。
但回答你的问题,大致上,我们可以说,在饥荒中,每三个哈萨克人中就有一个死亡。这就是数字。这个数字是巨大的,简直令人震惊。在幸存者中,我认为大约有一半人逃走了。因此,我们看到此时社会混合的庞大图景——人们逃往不同的地区。有些人逃往哈萨克斯坦境内,有些人逃往境外。当然,其中一些人绝对是饿死的。他们是赤贫人口。
其中还混杂着叛乱分子。但我认为,绝大多数人别无选择。粮食已经耗尽,他们一贫如洗,急需救济。哈萨克饥荒的严重程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与苏联同期发生的其他饥荒截然不同。
另一个解释大规模迁徙的因素是哈萨克人是游牧民族。作为游牧民族,他们经常选择逃亡,这是他们在危机时期用来逃避不利政治环境的策略。即使在这场饥荒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哈萨克人沿袭了历史上的迁徙路线。
问:但是,从我们掌握的数字来看,哈萨克游牧民族和定居者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
巨大。我还是要说,我们对哈萨克人的死亡人数没有一个准确而精确的估计。在我的书中,我使用了至少150万这个数字。一些哈萨克斯坦学者甚至认为死亡人数高达250万、350万。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
但即使根据我们现有的有限研究,也很清楚哈萨克人的命运与其他族裔的定居者有着天壤之别。我在书中估计,根据我查阅的一些研究,哈萨克斯坦公民死亡人数为150万,其中130万是哈萨克人。因此,如果看一下当时共和国民族平衡的比例,大约是60-40:60%是哈萨克人,40%是其他民族。但死亡人数中大约90%是哈萨克人。因此,受此影响的不成比例的是哈萨克人。
我认为一些乌克兰人口统计学家在更广泛的全国研究中稍微关注了哈萨克人的死亡人数问题。奥列格·沃洛维纳就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他的研究范围有些局限,因为他没有涵盖哈萨克饥荒的整个时期。他的研究只关注1932年,而就哈萨克的情况而言,1931年也有大量人口死亡。尽管如此,沃洛维纳还是得出结论,哈萨克人遭受了巨大损失。
1932-1934年饥荒时期的哈萨克人。图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国家视频和摄影文件档案馆
问:与苏联其他游牧地区相比,哈萨克斯坦的饥荒仍然最为严重。为什么哈萨克斯坦遭受的苦难最多,即使最初的情况在这些方面是相似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中一个挑战是,我们实际上没有对集体化进行很多很好的研究。例如,在布里亚特、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许多游牧地区,我们确实没有对饥荒进行很多详细的研究。有几个原因可能有助于解释这种差异。
其中一个原因是哈萨克斯坦被置于完全集体化的第一阶段。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其他地区则作为中亚局的一部分进行统治。因此,与不属于中亚局的哈萨克斯坦相比,它们由不同的行政机构管辖。
哈萨克地区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饥荒期间,布尔什维克开始大规模地派遣农民定居者,人数多达几十万。他们在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上修建了卡尔拉格(卡拉干达劳改营)和古拉格。因此,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
然而,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对这片土地的承载能力知之甚少。它看起来是个很大的地方,可以想象那里会有繁荣的绿地和大规模的畜牧场。我们想象中的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这种想法在后来也出现了。处女地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另一个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哈萨克斯坦本身的地理环境。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它不可能成为粮仓。土库曼斯坦则大部分是沙漠。所以它的地貌也截然不同。
1932-1934年饥荒时期的哈萨克人。图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国家视频和摄影文件档案馆
问:饥荒是如何结束的?过程是怎样的?环境条件改善还是中心开始帮助更多的人?战胜饥荒的过程是怎样的?
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他们确实做出了更多努力来对抗疾病。当时有各种计划为人们接种疫苗,以预防当时正在蔓延的一些疾病。他们减少了饥荒期间人们本应捐赠的部分谷物和肉类采购。他们还开始放宽之前实行的一些政策。就像乌克兰大饥荒一样,我们看到他们实行了非常严厉的政策,比如将村庄列入黑名单、禁止人们进入城市、关闭边境等等。我们看到他们放宽了一些政策。当时也向共和国提供了粮食援助,但那是1932年很晚的时候了。援助物资花了很长时间才送到人们手中。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运气好。1933年是个丰收年。他们当时天气很好。天气在哈萨克饥荒中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老派的说法可能是,天气导致了这场饥荒,也可能不是。莫斯科和其他地方曾多次警告说,草原地区农业高度不稳定。你可能会在一年里得到充足的降雨,而在下一年却降雨不足。但他们仍然决定发展定居农业,尽管他们被警告过。当集体化年代发生干旱时,他们仍然告诉哈萨克人,你们必须弥补短缺。他们根本不考虑天气因素。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天气并不是一个独立因素,不应该让斯大林为此承担责任。但1933年的天气更好。
戈洛什琴因粮食短缺而受到指责。饥荒末期,他在哈萨克斯坦失去了职位。莫斯科派来了一位亚美尼亚人列翁·米尔佐扬。可以说,米尔佐扬是一位更务实的管理者,略胜一筹。因此,他也许能够更好地缓和并减轻党的某些政策。
影响是巨大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游牧经济体系的丧失。饥荒过后,哈萨克人基本上成为一个定居社会,而不是一个季节性迁移的社会。说饥荒摧毁了游牧经济体系并不公平,因为我们现在仍然能看到一些游牧经济。饥荒摧毁了游牧经济体系,但我们仍然看到哈萨克人游牧生活方式的各个要素继续影响着哈萨克人。例如,哈萨克斯坦现政府试图将游牧生活作为有用的历史,并将其用于国家建设。
氏族是哈萨克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氏族既是社会纽带,也是经济纽带。我们仍然看到其中一些在哈萨克人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这是饥荒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
另一个原因是人口大规模迁移带来的这种混合。人们迁徙到共和国不同地区。在俄罗斯等地也有大量哈萨克侨民。这也是导致统计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要完成这项工作,你需要弄清楚谁死了。他们逃到哪里去了?他们在邻国死去了吗?他们留在邻国了吗?他们回来了吗?这很难弄清楚。所以我指出这一点。其中一些问题就是饥荒的关键特征。饥荒过后,哈萨克斯坦本身也变得更加城市化。
哈萨克人在自己的共和国变成了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饥荒加速并促成了共和国人口的急剧变化。我们看到莫斯科派遣更多的定居者,在哈萨克人曾经的牧场和家园定居。战后古拉格集中营的发展以及二战期间被驱逐者的到来也促成了人口结构的转变。饥荒加速并促成了这一非常激进的人口政策。它使哈萨克斯坦成为一个比以往更加多民族的社会,而哈萨克人则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
问:苏联解体后,饥荒问题浮出水面。那么,最初的政策是什么?政府是如何看待这场饥荒的?
人们对这场饥荒非常感兴趣。最初,人们用哈萨克语小说来讨论它。而在苏联解体后,人们对它的兴趣迅速高涨。为此,哈萨克斯坦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来调查此事。委员会宣布这场饥荒是一场种族灭绝。此外,人们还掀起了一波最初的浪潮。
这也是我们看到一些关于大饥荒的重要研究发表的时候。但经过十年的调查,人们对大饥荒的兴趣逐渐减弱。后来,大饥荒成为一个政治上更为敏感的话题。它被视为可能破坏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关系的事情。
问:它是否受到乌克兰记忆政治的影响,乌克兰政府的记忆政策是如何影响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
首先,我们确实需要对哈萨克饥荒的记忆进行深入研究。我一直鼓励有人去做这件事。在写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碰到了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对哈萨克饥荒的记忆。但这是另一个话题。想想看,关于乌克兰饥荒的记忆,我们有多少书。而关于哈萨克饥荒的书却少得可怜。这是一个研究不足的话题。
是的,我肯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的记忆或大饥荒的政治影响了哈萨克的情况。例如,我看到一些哈萨克学者提到哈萨克大饥荒,称其为哈萨克斯坦大饥荒。所以他们会自觉地提到这一点。此外,哈萨克斯坦的许多政治家提到,不应该将哈萨克大饥荒政治化。他们没有直接提到大饥荒,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唤起人们对乌克兰大饥荒的记忆。他们说我们应该避免将历史政治化。
在哈萨克斯坦的案例中,大饥荒还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我在关于乌克兰饥荒的文献中看到一种观点,将内战饥荒和乌克兰饥荒联系起来,作为乌克兰苦难的一个共同叙述。最近,我看到哈萨克斯坦的学者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把内战和集体化期间发生的饥荒放在一个共同的苦难视角下。我相信这是受乌克兰人对乌克兰大饥荒的看法的影响。
不幸的是,如今在哈萨克斯坦研究哈萨克大饥荒的学者并不多。如果你是哈萨克斯坦的年轻学者,并希望在此领域有所建树,那么这个话题并不理想。许多年轻学者告诉我,如果你选择这个话题,也许你可以做到,但你会不断遇到问题。我们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哈萨克斯坦老一辈学者撰写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其中一些人已经去世。马利克·艾达尔·阿斯利别科夫是研究哈萨克斯坦饥荒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已去世。年轻一代学者也不太愿意研究这个话题。
但我希望看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饥荒研究学者之间进行更多的对话。我还没有看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学者就这个话题进行交流的太多努力,我认为这真的很有趣,也很重要。
在西方,关于民族政策的讨论很多。但我认为这在哈萨克斯坦并不是大问题。他们不会这样提出问题。
我对环境史很感兴趣,但这不是许多研究哈萨克斯坦饥荒的学者所关注的领域。作为来自西方的学者,我也很幸运。我有幸能够花大量时间坐在档案馆里,日复一日地阅读。而哈萨克斯坦的许多学者却没有这种条件。此外,由于这个话题被认为非常敏感,他们不太可能获得资助,因为你需要政府资助才能从事这项工作。在哈萨克斯坦的档案馆里做长期项目,不太可能获得政府资助。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有时间,而哈萨克斯坦的许多学者却没有。
问:您或哈萨克斯坦的学者在查阅档案时遇到过问题吗?也许有些东西被封锁了?
与乌克兰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哈萨克斯坦的秘密警察档案馆是不开放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因此,如果我们将有关乌克兰大饥荒和哈萨克斯坦大饥荒的信息量作比较,会发现它们并不相等。我们没有那些秘密警察档案,还有一些其他收藏品仍然不开放。在哈萨克斯坦,解密文件方面确实有很多进展。我很幸运能在书中使用其中一些收藏品,但许多收藏品仍然不开放。
问:您的书被翻译成俄语和哈萨克语。您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都收到了怎样的反响?也许,一些宝贵的批评?
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我完全被这种反响所震撼。我认为这本书的翻译版本比英文版本更受欢迎。作为作者,这让我深感谦卑。我所期待的最好回报就是该地区的读者能够阅读这本书。哈萨克斯坦的反响非常积极。我非常担心我的某些观点在哈萨克斯坦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但许多哈萨克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美国作家对这一话题的描述。因此,是我将这一话题带到了世界舞台。总的来说,我得到的关注是非常感激和赞赏的。
在我出版这本书之前,年轻一代也对这场饥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年轻一代对利用历史作为工具来消除本国过去的殖民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我的书在哈萨克斯坦大受欢迎,人们对历史以及审查苏联过去的罪行有着非常大的兴趣和活力。因此这本书真的火了。一时间,这本书风靡全国。它还以多种版本和版本出版。我认为这本书的哈萨克语译本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人说,看,我可以用俄语读这本书,但我想要用哈萨克语读。因此,用哈萨克语阅读本身就是一种非殖民化的行为,是对俄罗斯压迫的宣言。
俄罗斯政府的反应并不积极。人们会对一本书产生各种想象。他们并没有真正阅读这本书。因此,他们都觉得我是美国国务院的特工,试图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制造分裂,并“在哈萨克斯坦制造乌克兰的局势”。我受到了俄罗斯国家媒体上所有这些人的批评和攻击。他们的立场并不积极。但我还是想明白他们到底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因为那并不是我试图表达的观点。但毫无疑问,这本书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关注。这很好。
采访人:雅罗斯拉夫·科瓦楚克,阿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他专攻乌克兰西部的苏联历史。
日新说深耕国际议题,秉持普世价值与人文精神,致力于多元视角讲述与思考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