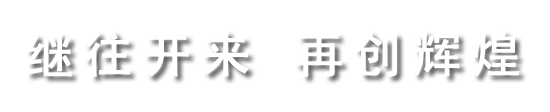《全景式数字游民报告》正式对外发布!在乡野而非庙堂探寻更多可能
近年,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一词在国内盛行。它背后代表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在审视自我价值追求后,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探求平衡,从“两点一线”延伸至“远方和旷野”,轻盈地找寻着自己的“大地工位”。
“数字游民”这一概念越来越火,社会化媒体上有网友戏言,“再多几个数字游民,连‘离职赛道’都变卷了”。
但定义却似乎越来越模糊——国内的“数字游民”都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工作方式有何不同?他们又怎么样看待未来,对此有哪些期待和想象?
为了可以呈现出本土数字游民更真实全面的状态、挑战与机遇,面向数字游民、创业者及其探索者的NCC共居共创社区首次发起了本次《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并联合十余个国内外游民社区进行问卷收集和传播。希望在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之外,能让更多的人关注“数字游民”,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本次问卷以线上形式进行发放,并联合十余个数字游民社区进行传播,公开招募对数字游民感兴趣的参与者填写问卷。最终数据如下:
在“内卷”“996”的社会背景下,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带来的技术革新影响,让“数字游民”这一概念在2020年开始,伴随着“旷野想象”在社交平台与新闻媒体报道中不断涌现、逐步升温,形成国内当下的“数字游民热”。
在各类媒体上,数字游民通常被塑造为「快乐的千禧一代自由职业者」。他们积极“出逃”,在乡野、在户外、在天地之间,找寻新的人生意义。
在探索者这一群体中,有17.05%的人进入职场不到一年,远高于数字游民中的职场新人比例(7.45%)。或许是因为慢慢的变多的青年开始意识到,传统的工作和生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他们虽未完全实现数字远程工作,但已展现出对游牧生活的渴望,甚至正在部分实践此类生活方式。随着年轻人对工作与生活的理念不断革新,他们的潜力与影响力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数字游民状态让人“上瘾”——当你成为数字游民越久,重回固定地点上班的意愿越弱。慢慢的变成了数字游民3年及以上的人 ,拒绝回到原有坐班状态的想法慢慢的变坚定(55.17%)。
但其实,对于数字游民来说,虽不再把“稳定”奉为理所当然的“正确”,但依然有部分伙伴保留着对稳定归宿的向往。
「随缘定居」——这不仅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上,还包括对自我价值感的重构。虽然数字游民拥抱流动和不确定性,但仍有近半数的人保留着对归宿的向往,也希望能遇见一个未来伴侣一起游牧。这种向往原因是长期流动带来的疲惫,频繁变动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传统观念下对家庭的想象等。
关于数字游民最大的滤镜之一,就是“别人上班我(看似)旅游”,“别人休息我还在休息”,这些工作日还在大胆发圈的人,都让大家心里有一个疑问:“天天不上班,到底怎么挣钱?”
事实上,“抽空工作的数字游民们”,只是“把赚钱的方式灵活化”,才能留出时间看世界。自由流动的游牧状态,让数字游民处于工作与休闲的动态平衡之中。
另一方面,数字游民这一概念在国内发展时间比较短,尚有许多支持和设施等待配齐。相较海外,国内远程全职工作的数字游民只占五分之一(22.34%)。怎样提供更好的环境去探索?怎样获得户籍和养老医疗等整套系统的支持;怎么为数字游民们提供更多的远程工作机会?怎样跟在地产生更强的链接?……
对于潜在的数字游民来说,找到新机会的需求最为迫切(38.01%),扩展社交和实现长期驻地的可能也成为重点。
数字游民提供了非常多“社会时钟”之外的参考样本,但他们的发展路径与传统职业发展截然不同。当慢慢的变多年轻人关注数字游民,探讨数字游民的未来职业发展、潜力及挑战显得很重要。
以往我们提“生产”二字,通常指的是“物质生产”,即拥有生产资料才能进行的生产活动。如今在一个“人人都是创作者”的年代,传统的物质生产正逐步被信息和知识生产所取代。中国本土的数字游民正在经历野蛮生长的1.0时代,他们一边自由创造一边怀有困惑。
据智联研究院的报告数据显示,七成以上的00后期望成为“数字游民”。这些潜在的年轻探索者群体很庞大,他们在观望中做出抉择。
2024三七互娱与“大黄山”品牌联动创新发展大会举办!大黄山游戏产业研究分院揭牌
“青”耕硕果 “企”愿丰收|2024年乡野耘间爱心良田丰收节在黄山成功举办